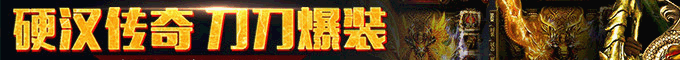贝聿铭的少年时代:从那一刻起,我开始想做建筑师
撰文︱李菁 贾冬婷
整理 | 余雅琴
贝聿铭这个名字,似乎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存在,他在今年五月去世,随之为自己一个世纪关于海外华人的传奇画上句号。与之相联系的那些建筑物——卢浮宫金字塔、香山饭店、苏州博物馆,都被时间证明了永恒性。某种意义上,建筑与我们面对的一些重要问题息息相关——权力、荣耀、记忆、身份……
一个建筑师是如何通过建筑来回应这些终极问题,并将它们带到永恒的?超越建筑师身份之外,贝聿铭又是如何见证和参与这一个世纪的历史的?在贝聿铭所见证的这个世纪之初,东方和西方曾爆发过相互交流和碰撞的“火柴热”,这场文化的发酵延续至今……在这个过程中,要抛弃什么,要坚守什么?如何在全球化环境下建立一种既包容又自我的视野?对这些问题的思考,正是这本关于贝聿铭及其家族的书《百年贝聿铭:东方与西方,权力和荣耀》希望带读者走近贝聿铭的原因。
这是一部基于实地采访的贝聿铭传记,改编自《三联生活周刊》贝聿铭主题封面故事。在组稿过程中,两位作者在纽约的贝氏事务所拜访了贝聿铭的两个儿子,听他们讲述了作为建筑师和父亲的贝聿铭;见到了贝聿铭的几位助手、项目参与者和传记作者,还原了他的成名史、他最重要作品 的出炉过程;去上海和苏州寻访了贝聿铭和贝氏家族的生活史,并实地探访了贝聿铭晚年在中国的作品,以图还原他对中国现代建筑语言的思考和实践;还询问了包括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在内的“大卢浮宫”项目参与者,解密了贝聿铭这一转折性作品三十年来的争议与和解。
两位作者以可贵的记者视角展现了贝聿铭的一生。书中的贝聿铭是个“普通人”:从学生时代到成人世界,憧憬过未来,怀疑过现实;换过专业,遇到过恩师;选择毕业去向时曾几经犹豫又备受质疑,在看似平顺的职业生涯中经历过大大小小的风波和危机……借着阅读贝聿铭反观自己和周遭世界,能给我们,尤其是年轻读者,以实实在在的启迪。在成书过程中,作者在原刊内容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和修订,尤其是新增了对贝聿铭部分代表性建筑作品的记述,是为了解贝聿铭晚年建筑成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,增强了传记作品的丰富性和完整性。这既是一部贝聿铭的成长传记,又是一部贝聿铭建筑设计作品的编年史传。

《百年贝聿铭》,李菁 贾冬婷 著,三联生活书店2019年8月版。
少年的新世界
一直到17岁离开中国,贝聿铭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。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,正是黄金时代。自开埠以来,这个曾经的小渔村依托长江出海口的地理优势,一头连接着西方,一头连接着供给橡胶、煤、大豆、石油、面粉、棉花、丝绸、烟草等的中国内陆城市,成为一个华洋杂处、东西碰撞的远东第一大城市。
乘坐汽船沿黄浦江蜿蜒而上,映入眼帘的上海标志就是外滩。买卖商品所积累起来的财富需要相应的服务,于是上百家银行在上世纪初应运而生,尤以外滩为聚集地。
直到今天,这条江边大道还保留着“万国建筑博览”的原貌,各种气势宏伟的花岗岩建筑鳞次栉比,尤以海关大楼、汇丰银行、和平饭店、中国银行为代表。而23号的中国银行,是外滩众多建筑中唯一一幢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大楼,看上去和周围建筑风格一致,又融入了很多中国风格的细节,比如传统建筑式样的方形尖顶,栏杆和窗格处的镂空民族图样,是近代建筑东西结合的一个典范。不过,1927 年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从香港来到上海管理中国银行时,这里还只是在德国总会旧楼基础上改建的营业楼,新楼从1934年才开始动工。

中银大厦。
在上海,贝祖诒加入了一帮具有现代思想的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的小集团,这个小集团以宋子文为中心。他们意识到,要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境地,以一个提倡贸易、工业、现代教育和西式礼仪的新式中国逐渐取代旧中国,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外汇领域维护自己的地位。在香港的十年磨炼已经使贝祖诒成为外汇业务专家,1930 年中国银行总处成立国外部,由贝祖诒兼任主任。此后,他在所有的商业港口开办外汇交易业务,并在世界各地开设了18家中国银行分行。住在租界区的贝家当时的生活也是西式的:贝祖诒总是穿着高领西装,梳着分头,参加俱乐部,打高尔夫球。
贝聿铭在2000年后设计苏州博物馆期间去上海时,曾去寻访以前住过的地方。他去了南京路和石门二路交界的圆弧形转角大楼,那里原来是中银宿舍;又去了后来居住的武康路378号,当时贝家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陈立夫、国民党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果夫、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等人是一条马路上的近邻。不过,如今再去寻访,这里已经改造成了艺术家、设计师、精品店汇集的时尚街区“武康庭”,以前的大部分花园洋房还在,但贝家那幢被拆除了。还有一处是南阳路170号的“贝家花园”,如今用作一个餐厅和精品酒店。
这幢钢混结构的小楼建于1934年,带有特殊的装饰艺术风格。从南入口进入,先是一个花园,其中假山、小桥、池塘、葡萄架等一应俱全,中央一座五角亭尤为特别,据说是寓意五行,而其中属金的一角正对大门。主楼为三层,酒店人员指引我从一侧“龙梯”向上参观。所谓“龙梯”是入口处雕刻的龙形装饰,楼梯从这里盘旋而上。而旁边一侧还有一部电梯,据说是上海第一部OTIS
(奥的斯)
电梯,现在仍可使用。主副楼之间的门廊照壁上也别有洞天,刻有一百个不同的篆体“寿”字。而附近不远处的铜仁路333号也和贝家有关,这里是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在上海的最后一个作品——著名的“绿房子”,一度是贝润生的五女婿吴同文的私宅。
位于上海南阳路170号的贝祖贻旧居“贝家花园” ,蔡小川摄。
贝聿铭初中在上海青年会中学就读,高中则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。当时的圣约翰中学是美国圣公会教徒开办的一所昂贵的寄宿学校,致力于用西方的价值观教导中国上层家庭的孩子,贝聿铭在学校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贝聿铭后来回忆,他在上海接触了新的建筑、艺术和生活方式,会在周末和朋友们乘车去闹市区,常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,或者去桌球房打桌球。